2024年8月17日晚,全國(guó)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cháng)、中(zhōng)國(guó)科(kē)學(xué)院原院長(cháng)、“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周光召院士,因病醫(y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
“正在準備周光召老所長(cháng)的追思會。”中(zhōng)國(guó)科(kē)學(xué)院理(lǐ)論物(wù)理(lǐ)研究所綜合處處長(cháng)安(ān)慧敏幾度哽咽。在學(xué)術圈外,很(hěn)少有(yǒu)人知道,周光召還曾是中(zhōng)國(guó)科(kē)學(xué)院理(lǐ)論物(wù)理(lǐ)研究所的老所長(cháng),研究所樓宇顯著位置懸挂的“開放、流動、聯合、競争”辦(bàn)所方針和“開放、交融、求真、創新(xīn)”辦(bàn)所理(lǐ)念都是周光召提出的。
他(tā)生于戰亂年代,成就于動蕩時期,在中(zhōng)國(guó)的第一顆原子彈、第一顆氫彈和戰略核武器的研究設計方面做出了大量重要工(gōng)作(zuò)。
周光召不僅是理(lǐ)論物(wù)理(lǐ)學(xué)家,擔任行政領導後,為(wèi)中(zhōng)國(guó)科(kē)學(xué)和技(jì )術的發展起了重要作(zuò)用(yò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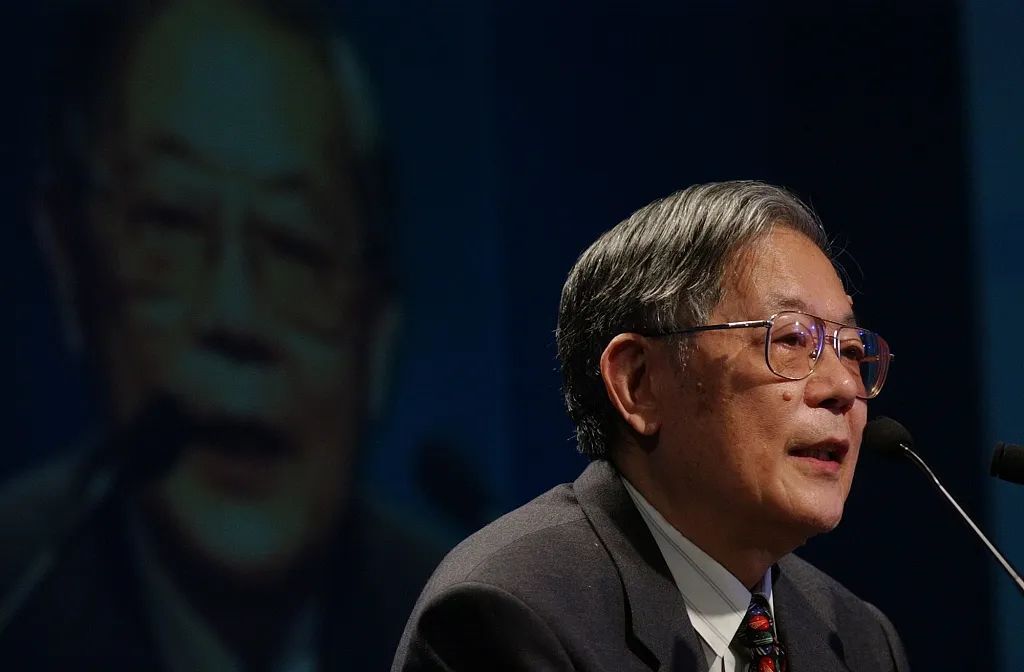
科(kē)學(xué)家周光召 圖/視覺中(zhōng)國(guó)
臨危受命
原中(zhōng)國(guó)科(kē)學(xué)院副秘書長(cháng)曹效業記述,1984年前後在中(zhōng)科(kē)院流傳着一個故事:當時一位領導指責中(zhōng)科(kē)院“不冒泡”,為(wèi)此中(zhōng)科(kē)院院長(cháng)盧嘉錫拍了桌子,說我頭上有(yǒu)兩頂帽子,一頂叫院長(cháng),你們可(kě)以拿(ná)走,一頂叫先生,那是拿(ná)不走的。
當時中(zhōng)科(kē)院面臨的外部壓力除了高層對其脫離國(guó)民(mín)經濟建設的批判,還有(yǒu)高校取代中(zhōng)科(kē)院從事基礎研究的呼聲,“取消中(zhōng)科(kē)院”的輿論傳了一波又(yòu)一波。同時,重理(lǐ)論輕實踐、重基礎輕應用(yòng)、人員不流通、管理(lǐ)體(tǐ)系僵化等内部問題也逐漸暴露。“盧嘉錫在1985年工(gōng)作(zuò)會議上擊案疾呼:中(zhōng)科(kē)院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曾任中(zhōng)國(guó)科(kē)學(xué)院學(xué)部聯合辦(bàn)公(gōng)室副主任的周先路寫道。
1984年4月被推任中(zhōng)科(kē)院副院長(cháng)時,周光召已經55歲,頗有(yǒu)些臨危受命的意味。“當時,我對自己承擔這個工(gōng)作(zuò)是否合适,心裏一直在打鼓,直到現在還在鬥争。”周光召在1985年1月11日上午的中(zhōng)科(kē)院工(gōng)作(zuò)會議上說。7個月前,他(tā)剛到中(zhōng)科(kē)院就感到了“危機感”,經過大半年調研,他(tā)犀利地提出,“按現存的模式,中(zhōng)國(guó)科(kē)學(xué)院能(néng)否繼續存在是值得懷疑的。”
中(zhōng)國(guó)按照蘇聯模式建立了科(kē)學(xué)院,而蘇聯模式是“一個與工(gōng)業生産(chǎn)相脫離的而且本身不流動的模式”。周光召很(hěn)清楚,蘇聯的科(kē)學(xué)技(jì )術在某些理(lǐ)論領域達到世界前列,但它的很(hěn)多(duō)科(kē)學(xué)技(jì )術卻落後于西方先進國(guó)家。這一模式的弊端也逐漸在中(zhōng)國(guó)顯現。
周光召把問題症結引向了體(tǐ)制層面。他(tā)說,随着中(zhōng)國(guó)經濟體(tǐ)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必然對科(kē)技(jì )發展有(yǒu)更大的激勵。假如中(zhōng)國(guó)所有(yǒu)的企業都不是30年一貫制,而是從市場、從顧客的要求出發,就必然要更新(xīn)産(chǎn)品,必然對技(jì )術革新(xīn)提出新(xīn)要求,這就必然對科(kē)學(xué)技(jì )術的發展提供更大的動力和機會。
“如我們科(kē)學(xué)院的同志(zhì)不從思想上、觀念上,管理(lǐ)方法上來一個根本性變革,那在全國(guó)科(kē)學(xué)技(jì )術向前發展的同時,我們有(yǒu)很(hěn)多(duō)研究所可(kě)能(néng)會走向萎縮。”周光召随即介紹了美國(guó)、蘇聯的科(kē)技(jì )發展模式,還有(yǒu)中(zhōng)間的德(dé)國(guó)、日本模式,并提出“思考中(zhōng)國(guó)的模式”。
周光召當時提出“以進攻的姿勢”“适應新(xīn)形勢”,也給出了一些解決問題的具(jù)體(tǐ)方案。例如,根據科(kē)學(xué)院研究的性質(zhì)分(fēn)門别類地進行管理(lǐ),而不能(néng)像過去那樣一刀(dāo)切;建立開放實驗室、開放研究所,把科(kē)學(xué)院建成全國(guó)的自然科(kē)學(xué)研究綜合中(zhōng)心,面向全國(guó)吸引人才;鼓勵科(kē)技(jì )人員辦(bàn)公(gōng)司,但不要忘記辦(bàn)公(gōng)司的根本目的是要為(wèi)發展中(zhōng)國(guó)科(kē)學(xué)和經濟服務(wù)。
“光召在1985年1月中(zhōng)科(kē)院工(gōng)作(zuò)會議上談到的對中(zhōng)科(kē)院改革的想法,就是後來全國(guó)科(kē)技(jì )體(tǐ)制改革的設計思路。”郭傳傑說。
當時社會盛行“實用(yòng)主義”,計算所裏那些曾為(wèi)“兩彈一星”研發貢獻關鍵作(zuò)用(yòng)的大型計算機此刻不過是“一隻隻不會下蛋的公(gōng)雞”,不能(néng)轉化為(wèi)商(shāng)品,不能(néng)創造利益。
時任計算所所長(cháng)曾茂朝比較開明,那時已經支持下屬創辦(bàn)了二十多(duō)家公(gōng)司,但他(tā)仍無法接受這個創造了無數輝煌的大型計算所被一家剛成立不久的民(mín)營科(kē)技(jì )公(gōng)司承包,更無法接受所裏一千五百名(míng)科(kē)研工(gōng)作(zuò)者或被遣散或被買斷的結局。
讓一家民(mín)營公(gōng)司承包計算所,“這不是在我頭上插一根雞毛,拿(ná)到街(jiē)上給買了嗎!” 曾茂朝不無悲憤地在報告中(zhōng)寫道。随即他(tā)請求“承包計算所”,并順勢提出一個條件,“請不要再用(yòng)國(guó)家研究所的标準來要求我。”
1985年夏天,這份關乎中(zhōng)國(guó)科(kē)學(xué)院計算技(jì )術研究所命運的報告交到了周光召的手上。身為(wèi)兩彈一星元勳,又(yòu)經曆過動蕩十年,周光召理(lǐ)解老一代科(kē)學(xué)家迫切希望搞基礎研究的願望,同時作(zuò)為(wèi)在上世紀80年代出訪歐美的學(xué)者,他(tā)又(yòu)看到中(zhōng)國(guó)科(kē)學(xué)技(jì )術改革的大勢所趨。不論是被民(mín)營公(gōng)司承包,還是研究人員出走,周光召不同意采取任何極端措施來解決問題,他(tā)的新(xīn)提議最終得到了院長(cháng)會議的支持:批準一部分(fēn)科(kē)學(xué)家走出研究所。
周光召馬上轉告曾茂朝,作(zuò)為(wèi)一所之長(cháng),曾茂朝仍會擁有(yǒu)他(tā)的研究所和技(jì )術人員,但他(tā)必須為(wèi)自己找到出路。
一院兩制
1984年開始在中(zhōng)科(kē)院試行的“所長(cháng)負責制”也被正式确定下來。這一制度賦予研究機構幹部人事管理(lǐ)上的自主權,科(kē)研院所可(kě)以自主決定内設機構和人事管理(lǐ)事宜,充分(fēn)尊重和發揮科(kē)學(xué)技(jì )術人員的作(zuò)用(yòng)。
“也許可(kě)以說,中(zhōng)國(guó)科(kē)學(xué)院近30年以來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是确立所長(cháng)負責制。這個改革,對于中(zhōng)科(kē)院的發展,迄今仍然起到重要作(zuò)用(yòng)。”首都醫(yī)科(kē)大學(xué)校長(cháng)饒毅在紀念文(wén)章中(zhōng)寫道。
1986年底,中(zhōng)央有(yǒu)關領導找盧嘉錫和周光召談話,明确由周光召擔任中(zhōng)科(kē)院院長(cháng)和黨組書記。次日,周光召着手指導科(kē)學(xué)院改革方案,曹效業記得那天周光召穿了一件深色羽絨服,他(tā)如往常脫稿演講一樣,闡述他(tā)對中(zhōng)科(kē)院改革發展的構想,曹效業與另兩位同事則負責将周光召的思想整理(lǐ)成文(wén)字。這份題為(wèi)“關于中(zhōng)國(guó)科(kē)學(xué)院進一步改革的請示”,很(hěn)快得到了國(guó)務(wù)院主要領導的批準。
到1987年,中(zhōng)科(kē)院的辦(bàn)院方針初步成型。最終在1992年1月頒發的《中(zhōng)國(guó)科(kē)學(xué)院科(kē)技(jì )政策綱要》中(zhōng),方針被進一步完善為(wèi):把主要力量動員和組織到為(wèi)國(guó)民(mín)經濟和社會發展服務(wù)的主戰場,同時保持一支精(jīng)幹力量從事基礎研究和高技(jì )術創新(xīn),即“一院兩制”,這成為(wèi)周光召在中(zhōng)科(kē)院改革的主線(xiàn)。
周光召認為(wèi),中(zhōng)科(kē)院過去隻重視科(kē)學(xué)本身的動力,以及公(gōng)益性質(zhì)為(wèi)主的國(guó)家任務(wù),包括軍工(gōng)、攻關等,這是科(kē)學(xué)院發展的主要動力。而未來的科(kē)學(xué)院,要在商(shāng)品經濟環境中(zhōng)為(wèi)經濟建設服務(wù),在科(kē)學(xué)本身的推動力之外,還需要增添市場的動力,通過另一種機制來推動研究工(gōng)作(zuò)。
“光召院長(cháng)上任後,成立了科(kē)技(jì )政策局,他(tā)親自分(fēn)管,帶我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周口店(diàn)猿人遺址讀了一個星期的經濟學(xué),讀本是一套諾貝爾經濟學(xué)獎獲得者的代表作(zuò)。”曹效業回憶。當時周光召提出“以研究所為(wèi)基本單位”的改革思路,後來實踐證明,這一思路幫助各研究所順利度過經濟緊缺時期,中(zhōng)科(kē)院這支國(guó)家隊因此得以保存下來。
在基礎研究領域,周光召提出“開放、流動、聯合、競争”的方針,并在中(zhōng)科(kē)院首先建立了開放實驗室,由此促成了國(guó)家重點實驗室布局的形成。随着中(zhōng)科(kē)院改革的方針、體(tǐ)制問題基本确定,周光召将主要精(jīng)力集中(zhōng)到了人才問題上。他(tā)在1990年主持召開了全國(guó)首次青年科(kē)技(jì )人才工(gōng)作(zuò)會議,提出“必須在10年之内,逐步把第一線(xiàn)科(kē)研工(gōng)作(zuò)轉交給年輕一代”“順利完成科(kē)研重擔代際轉移”的戰略目标。
“周先生發現和支持很(hěn)多(duō)年輕人,判斷他(tā)們的專長(cháng),看中(zhōng)他(tā)們的才華和人品,了解他(tā)們的需求,支持尚未得到廣泛認可(kě)的一線(xiàn)科(kē)學(xué)工(gōng)作(zuò)者和技(jì )術發明者。”饒毅回憶。
“完美的儒家思想的踐行者”
1987年5月下旬的一天,郭傳傑突然接到陪同周光召到沈陽分(fēn)院調研的通知。郭傳傑已經在中(zhōng)科(kē)院化學(xué)研究所埋頭研究了17年,原本就不情願被調任到機關部門,他(tā)又(yòu)比較怕與領導接觸。在沈陽出差的三四天,沒和周光召說過一句話。
“光召平時不苟言笑,别人和他(tā)講話時,他(tā)可(kě)能(néng)邊聽、邊思考、邊把想法寫下來,所以不熟悉他(tā)的人,可(kě)能(néng)會覺得他(tā)高冷。”郭傳傑說。周光召一米七幾的身高,中(zhōng)等身材,經典的二八分(fēn)發型,他(tā)習慣把頭發梳向右側,早年常戴一副黑框茶色眼鏡,一思考問題就眉頭緊鎖。
直到從沈陽回到北京機場,周光召問他(tā)“這次跑了不少所,印象怎麽樣?”郭傳傑才開口說了幾句:“我是做基礎研究的,特别是對科(kē)技(jì )人員搞公(gōng)司有(yǒu)一些看法,覺得那是倒買倒賣。中(zhōng)關村辦(bàn)了不少公(gōng)司,社會上說那是‘騙子一條街(jiē)’。”
“那現在呢(ne)?”周光召笑了,接着問。“好像有(yǒu)點不一樣,改革有(yǒu)改革的道理(lǐ)。”郭傳傑說。調研期間,像郭傳傑這樣對改革不理(lǐ)解的科(kē)技(jì )人員很(hěn)多(duō),每次參觀座談,周光召都要苦口婆心地講科(kē)技(jì )體(tǐ)制改革的原因,講科(kē)學(xué)技(jì )術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律。
“光召強調遵循客觀規律,同時強調對人的尊重。因此,那個時期,雖然改革力度很(hěn)大,但留下的後遺症較少。”郭傳傑說。
改革開始後,社會上出現很(hěn)多(duō)激進的口号,如讓科(kē)技(jì )人員“斷奶”下海,“不換腦袋就換人”。周光召是十分(fēn)堅定的改革派,但他(tā)很(hěn)反對這種傷人的說法和做法。他(tā)多(duō)次在會議上說:“對我們的科(kē)技(jì )人員,要充分(fēn)信任他(tā)們,要對他(tā)們願意為(wèi)國(guó)家經濟建設和科(kē)技(jì )發展做貢獻的根本積極性有(yǒu)足夠評價。目前,他(tā)們中(zhōng)的确有(yǒu)些同志(zhì)想不通,思想沒轉過彎來,甚至有(yǒu)怨言,有(yǒu)情緒。這正是我們要做工(gōng)作(zuò)的地方。”
周光召提出,對知識分(fēn)子,要引導他(tā)們自己想通。想不通,沒有(yǒu)自覺性,是不行的。沒想通,甯可(kě)等等,再做做工(gōng)作(zuò),不能(néng)硬逼。因此,周光召曾經多(duō)次在各種場合對科(kē)技(jì )體(tǐ)制改革的必要性和意義進行抽絲剝繭式的分(fēn)析。
“周光召以中(zhōng)科(kē)院院長(cháng)身份保護科(kē)學(xué)家、穩定中(zhōng)科(kē)院所講的話,讓中(zhōng)科(kē)院同仁都非常感佩。”諾貝爾物(wù)理(lǐ)學(xué)獎獲得者、中(zhōng)科(kē)院外籍院士楊振甯說,他(tā)曾評價周光召是“一個完美的儒家思想踐行者”。
1961年,周光召已經在蘇聯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獲得了兩次科(kē)研獎金,聽說蘇聯撤走在華專家後,他(tā)主動打報告回國(guó)從事核武研究。1984年,正在歐洲遊學(xué)的周光召再次“奉召”回國(guó),旋即被任命為(wèi)中(zhōng)科(kē)院副院長(cháng)。
“基礎研究隻有(yǒu)第一,沒有(yǒu)第二”
楊振甯第一次聽說周光召這個名(míng)字是在20世紀50年代末,美國(guó)高能(néng)物(wù)理(lǐ)領域的人都知道,周光召是“當時最傑出、最有(yǒu)新(xīn)思想的物(wù)理(lǐ)學(xué)家之一”。當時國(guó)外報道稱:“周光召的成果震動了杜布納。”
1957年春天,28歲的周光召被國(guó)家派往蘇聯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從事粒子物(wù)理(lǐ)方面的基礎研究。在一次讨論會上,周光召對莫斯科(kē)大學(xué)一位教授在高能(néng)物(wù)理(lǐ)前沿的課題“相對性粒子的自旋結果”提出異議,但未得到這位權威和他(tā)同事的認同或重視。随後,周光召用(yòng)不到100天的時間獨立研究分(fēn)析,嚴格論證了蘇聯專家的結果是錯誤的。他(tā)們二人後來因此成為(wèi)很(hěn)好的朋友。
半個世紀後,周光召與北大同事、後來任北大校長(cháng)的陳佳洱在一次談話中(zhōng)提到,“我國(guó)自古以來缺少一種質(zhì)疑權威和追根究底的精(jīng)神”。而周光召挑戰權威的意識源于他(tā)的家庭教育。
1929年5月,周光召出生在湖(hú)南一個溫馨、重教而又(yòu)無拘無束的家庭。1951年,周光召以優異的成績大學(xué)畢業,進入清華研究院,師從理(lǐ)論物(wù)理(lǐ)學(xué)家彭桓武教授。1952年院系調整,周光召跟随彭桓武到北京大學(xué)繼續研究生學(xué)業,兩年後畢業,留任北大。當時北大曾三次推薦他(tā)赴蘇深造,都因家庭和社會關系原因未被主管部門批準。
1957年2月,周光召以中(zhōng)方工(gōng)作(zuò)人員的身份被派往蘇聯。到1961年回國(guó),周光召在杜布納的4年裏,在國(guó)際著名(míng)學(xué)術刊物(wù)上發表了30篇學(xué)術研究論文(wén),幾乎全部是他(tā)一個人獨立或以他(tā)為(wèi)主完成的。他(tā)也因此先後兩次獲得聯合核子研究所的科(kē)研獎金。
多(duō)年後,周光召在科(kē)技(jì )體(tǐ)制改革時提出“基礎研究隻有(yǒu)第一,沒有(yǒu)第二”,強調科(kē)學(xué)前沿的概念,與他(tā)早年經曆不無關系。在杜布納的最後一年,周光召聽聞蘇聯突然撤走所有(yǒu)在華專家後,向國(guó)内打報告,要求立刻回國(guó)。
當時北大保留了周光召的工(gōng)作(zuò)關系,讓他(tā)每周花(huā)一天時間來學(xué)校工(gōng)作(zuò)。“我們都不知道,甚至也沒有(yǒu)深想,在周六以外的時間,光召在做什麽,但我們都感到一種精(jīng)神力量,而光召是這種力量的身體(tǐ)力行者。記得他(tā)曾講到,不少同事們曾為(wèi)不能(néng)發表文(wén)章感到遺憾。”中(zhōng)科(kē)院院士、原理(lǐ)論物(wù)理(lǐ)研究所所長(cháng)蘇肇冰應邀在《我們認識的光召同志(zhì)》一書中(zhōng)撰文(wén)回顧。
蘇肇冰不知道的是,周光召在回國(guó)當年就進入了第二機械工(gōng)業部第九研究院理(lǐ)論研究所,開始核武研究。周光召後來回憶,從杜布納回國(guó)後,很(hěn)多(duō)國(guó)外好友打聽不到他(tā)任何消息,還鬧了烏龍,傳說他(tā)在回國(guó)途中(zhōng)因飛機爆炸逝世了。
“求實與忘我的科(kē)學(xué)家品質(zhì)始終沒有(yǒu)改變”
1961年,周光召回國(guó)後不久,便在一次讨論中(zhōng) “一戰成名(míng)”。
當時原子彈的研究設計一度陷入困境。研究人員唯一可(kě)參考的内部資料是蘇聯專家對原子彈教學(xué)模型的簡介,由于一個關鍵物(wù)理(lǐ)量錯誤,内部進行了九次計算。周光召檢查分(fēn)析了全部計算結果,認為(wèi)計算無誤,懷疑蘇聯專家的數據不可(kě)靠,這在當時是非常大膽而具(jù)有(yǒu)挑戰性的判斷。
周光召用(yòng)最大功原理(lǐ),證明了内爆過程中(zhōng)無論如何都不能(néng)達到蘇聯專家給的壓力值,數據明顯是錯的,結束了近一年的争論與停滞。1962年年底前後,他(tā)協助鄧稼先完成并提交了中(zhōng)國(guó)第一顆原子彈的理(lǐ)論設計方案。
據參加原子彈研究的黃祖洽院士回憶,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時,鄧稼先去了基地,周光召留守北京。1964年10月15日,原子彈起爆的前一天,周光召接到前方指示,“為(wèi)确保萬無一失,把重要過程重新(xīn)計算一遍。”經過十幾個小(xiǎo)時的計算,“我們想,不成功的幾率大概小(xiǎo)于千分(fēn)之一。”周光召在一段央視紀錄片的采訪中(zhōng)回應說。
原子彈爆炸成功後,周光召的工(gōng)作(zuò)仍在繼續,還要研究氫彈的設計。
經過那段曆史,“一些人接受了教訓,因此很(hěn)少發表不同意見,但光召求實與忘我的科(kē)學(xué)家品質(zhì)始終沒有(yǒu)改變。”曾任中(zhōng)科(kē)院院士工(gōng)作(zuò)局領導成員的孟輝回憶。
1978年,楊振甯回國(guó)交流,住在北京飯店(diàn)。有(yǒu)一天被通知,時任副總理(lǐ)鄧小(xiǎo)平要請他(tā)吃飯,楊振甯當時已經知道要讨論關于造大加速器的問題。楊振甯本人不贊成造大加速器,但他(tā)也清楚國(guó)内造加速器的意願很(hěn)強烈,他(tā)特意請周光召和鄧稼先到北京飯店(diàn)吃早飯,征求意見。周光召慢慢地講:“你就應該照直講,有(yǒu)什麽意見就如實道來,這是最正确的政策。”給楊振甯留下了深刻印象。
21世紀到來前,包括周光召在内的23名(míng)科(kē)技(jì )專家被授予“兩彈一星功勳獎章”。《中(zhōng)國(guó)原子彈的制造》一書記載:中(zhōng)國(guó)通過閱讀外國(guó)文(wén)獻學(xué)到的東西使他(tā)們了解了熱核反應所需要的材料,并且在1964年至1965年冬季,他(tā)們建成了一種主要熱核材料——氚化锂-6的生産(chǎn)線(xiàn)。周光召的夫人鄭愛琴,正是大量”外國(guó)文(wén)獻“的收集者和翻譯者之一。
鄭愛琴原本在北京東郊的一個研究所從事生物(wù)化學(xué)研究。盡管當時沒有(yǒu)像現在這樣堵車(chē),但是由于交通不發達,她和周光召的工(gōng)作(zuò)地點相距甚遠(yuǎn),為(wèi)支持周光召工(gōng)作(zuò),鄭愛琴放下當時炙手可(kě)熱的胰島素研究項目,加入九所,憑借她深厚的外文(wén)功底,開始做科(kē)技(jì )情報調研工(gōng)作(zuò)。
談及他(tā)們的獨女周瑩,周光召在九所的同事都感到“那是個讓人心疼的孩子”。父母工(gōng)作(zuò)緊張,常常顧不上她,遇到大人出差,周瑩得一個人做家務(wù),自己搬煤氣罐上樓。中(zhōng)學(xué)時代的周瑩遇上動蕩十年,16歲就當了工(gōng)人,後來通過考試進入大學(xué),又(yòu)通過考試出國(guó)留學(xué)。“我們對她的學(xué)習幾乎沒有(yǒu)任何幫助,主要都是靠她自己。”周光召說起女兒成長(cháng),總是流露出愧疚。
學(xué)者,“戰略家”
1979年底,周光召調到中(zhōng)科(kē)院理(lǐ)論物(wù)理(lǐ)所。在這前後幾年,周光召曾短暫回歸他(tā)心心念念的學(xué)術領域。
一天,周光召找到蘇肇冰,要把理(lǐ)論物(wù)理(lǐ)所的兩位科(kē)學(xué)家郝柏林和于渌請來一起做閉路格林函數,郝柏林和于渌後來均被評為(wèi)中(zhōng)科(kē)院院士。周光召和蘇肇冰有(yǒu)深厚的量子場論功底,郝柏林和于渌在平衡态相變和臨界現象方面有(yǒu)研究經驗,周光召決策把閉路格林函數首先用(yòng)于動态臨界現象的分(fēn)析,開啓了不少後繼工(gōng)作(zuò)的研究方向。
諾貝爾物(wù)理(lǐ)學(xué)獎獲得者、中(zhōng)科(kē)院外籍院士李政道曾總結他(tā)們的工(gōng)作(zuò):周光召與合作(zuò)者一起系統地發展了非平衡态統計的閉路格林函數,并嘗試把所發展的方法應用(yòng)到激光、等離子體(tǐ)、臨界力學(xué)、随機淬火系統等方面。
有(yǒu)關合作(zuò)研究長(cháng)達八年。中(zhōng)科(kē)院理(lǐ)論物(wù)理(lǐ)所學(xué)術委員會幾度準備推薦這項研究到院裏評獎,遭到周光召反對:“我擔着院、所領導,叫人家怎麽評?”這組工(gōng)作(zuò)一直拖到周光召卸去科(kē)學(xué)院院長(cháng)職務(wù)之後,1999年獲得了中(zhōng)科(kē)院自然科(kē)學(xué)獎一等獎和2000年國(guó)家自然科(kē)學(xué)獎二等獎。次年,美國(guó)科(kē)學(xué)信息研究所為(wèi)“周、蘇、郝、于”四人1985年發表在國(guó)際綜述雜志(zhì)上的長(cháng)篇文(wén)章頒發了“1981~1998年度經典引文(wén)獎”。
1980年,剛入選中(zhōng)科(kē)院院士的周光召應邀去美國(guó)弗吉尼亞大學(xué)和加州大學(xué)任客座教授。完成在美國(guó)一年的訪問計劃後,周光召又(yòu)受邀赴歐洲核子研究中(zhōng)心訪問,擔任研究員。
正在歐洲訪學(xué)的周光召突然被召回國(guó)。“與1960年代主動要求回國(guó)不同,這次多(duō)少有(yǒu)些不情願。”曹效業分(fēn)析。據當時中(zhōng)科(kē)院院士錢三強的秘書葛能(néng)全回憶,錢三強在辦(bàn)公(gōng)室與周光召就此事談了很(hěn)長(cháng)時間,周光召出來時眼圈有(yǒu)些紅。
“那時中(zhōng)科(kē)院已經危在旦夕,需要周光召,也隻有(yǒu)他(tā)能(néng)主持中(zhōng)科(kē)院的改革。”郭傳傑認為(wèi),周光召的回歸離不開彭桓武的推薦,和時任中(zhōng)科(kē)院院長(cháng)盧嘉錫的信任。就這樣,周光召再次告别學(xué)術研究,回到行政崗位。1984年,周光召擔任理(lǐ)論物(wù)理(lǐ)所所長(cháng),同時任中(zhōng)科(kē)院副院長(cháng),1987年1月任中(zhōng)科(kē)院院長(cháng)、黨組書記。1998年,周光召被選為(wèi)第九屆全國(guó)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cháng)。
“周老師的思考方式與衆不同,他(tā)總是從第一原理(lǐ)出發,自己推導,不輕信權威結論。我不知道他(tā)當時是否徹夜未眠來想這個問題。他(tā)一直關心理(lǐ)論物(wù)理(lǐ)前沿,貢獻了很(hěn)多(duō)卓越的學(xué)術想法,但他(tā)決不在他(tā)沒有(yǒu)做出實際工(gōng)作(zuò)的論文(wén)上署名(míng)。”周光召的學(xué)生、理(lǐ)論物(wù)理(lǐ)學(xué)家吳嶽良告訴《中(zhōng)國(guó)新(xīn)聞周刊》,周光召在成為(wèi)國(guó)家領導人之後,自覺精(jīng)力和時間不足以完成具(jù)體(tǐ)的研究工(gōng)作(zuò),沒有(yǒu)發表過自己署名(míng)的學(xué)術論文(wén)。
1990年代,周光召組織籌建了中(zhōng)國(guó)工(gōng)程院。當時中(zhōng)科(kē)院有(yǒu)人反對單獨成立工(gōng)程院。一次晚飯後散步時,周光召與郭傳傑談起這件事,周光召說:“歐美發達國(guó)家在成立科(kē)學(xué)院後也都成立了國(guó)家工(gōng)程院,工(gōng)程技(jì )術的重要性越來越得到社會重視,這是經濟發展必然趨勢,我們理(lǐ)應支持。”
2003年,國(guó)務(wù)院決定啓動制訂“國(guó)家中(zhōng)長(cháng)期科(kē)學(xué)和技(jì )術發展規劃”的戰略研究。陳佳洱擔任基礎研究專題第14專題組的組長(cháng),他(tā)深感責任重大,于是帶着專題研究組的幾個成員到周光召家求教。周光召提出的一些戰略思考,後來幫助陳佳洱等人理(lǐ)清了基礎科(kē)學(xué)戰略研究的思路和研究框架。
2011年11月15日下午,正在參加國(guó)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973計劃)顧問組專家會議的周光召,突發腦溢血,被緊急送往北京醫(yī)院搶救,此後長(cháng)時間躺在醫(yī)院病床上。
四個月後,香港“求是科(kē)技(jì )基金會”将首個“終身成就獎”頒給了周光召,以表彰他(tā)無可(kě)争議的學(xué)術成就,高山(shān)仰止的科(kē)學(xué)精(jīng)神,以及悲天憫人的人文(wén)情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考:《我們認識的光召同志(zhì)——周光召科(kē)學(xué)思想科(kē)學(xué)精(jīng)神論集》